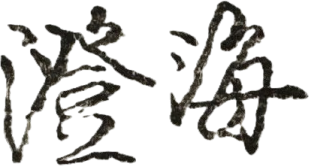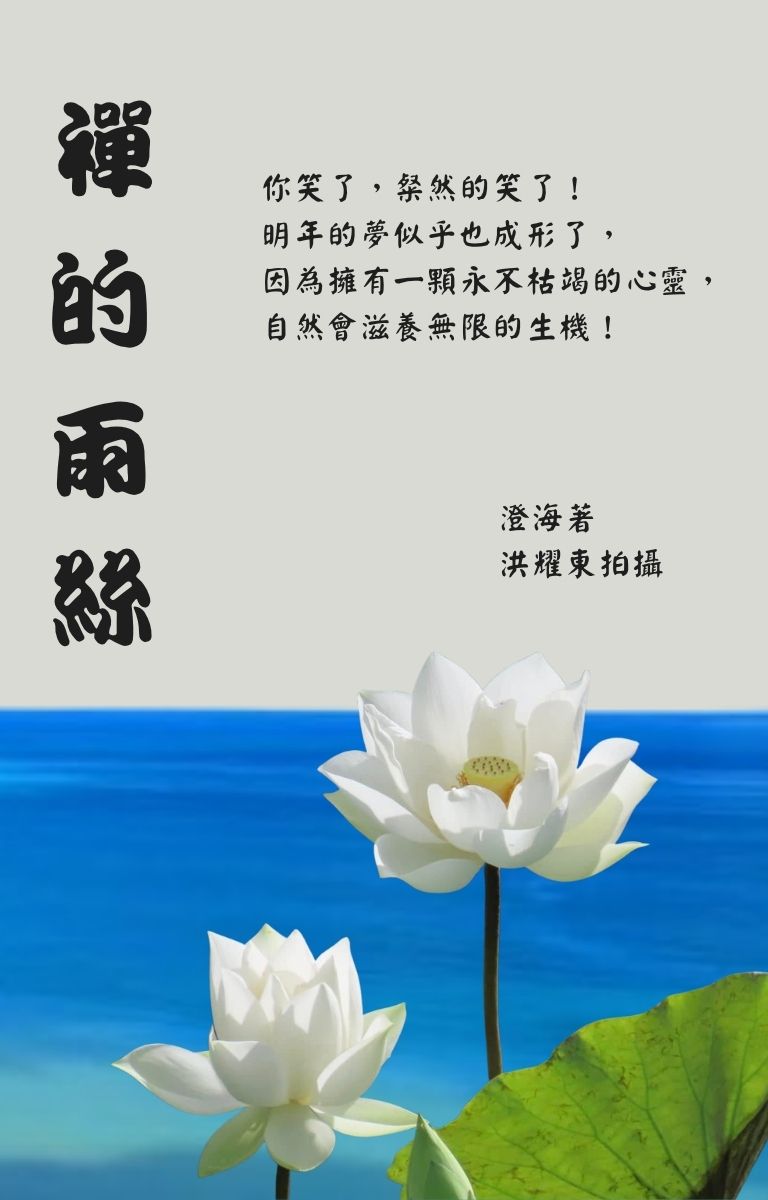十一、撥草探路
「茫茫撥草去追尋,水闊山遙路更深,
力盡神疲無覓處,但聞楓樹晚蟬吟。」
×× ×× ××
曲調有點蒼涼,深情款款地向遊子伸出溫暖的手,但那不是從口唱出來的,一遍又一遍從飄渺的心中唱出來的。你綻著沈寂而祥和的臉,說著說著心中就不停地迴盪著。
你覺得奇妙,你說壓根兒就沒想要刻意去唱,但自然地從心裡盪出節節的音符,不假思索。打從心裡我為你高興的,那是妙寶心,向多劫蒙塵遊子的呼喚,
就像望遠鏡在幽邈的太空中發現了新星,深沉的雀躍是故鄉人的盼望呀!
這是廓庵禪師〈牧牛圖頌〉的第一首。〈牧牛圖頌〉描寫修行人從初發心到圓滿境界的過程,那是「言語道斷,心行處滅」的,而初發心是珍貴的。
初發心就是將你的本心或自性,從累劫蒙塵的污垢中,撥開了一扇門,就像無盡藏尼師手把梅花嗅,剎那瑩光透閃,不可言傳只能意會。
略帶濕氣的微風掠過髮梢,遠遠一隻鷺鷥停在溪旁,岸草碧綠,雜花醇香,白得特別醒眼,白得讓你驚訝,也許就因為只有一隻,顯得仙風道骨。你靜靜地坐著,
聆聽從心中響起的韻律,是白的,純潔的白,空空朗朗的,宇宙廣闊卻澄明的,你說你感不到外境,外境似存在又不存在,歌好像唱了又像不唱,好像沉寂卻又活潑當機。
而你還是你。
但你又是誰呢?
你是生是死?
你感嘆竟然沒有人了解你浴火重生。其實,人又何必在乎別人會了解你?有時候我們都不了解自己,連自己怎樣來到這個世界都不知道,又何必一定要別人真的了解你呢?
這是一條無止境的探索,如果探索的火花熄滅了,生命力也枯萎了;當生命力枯萎了,活著只是生命現象的點綴,頭沒頭出。
黃龍海機禪師就擁有一顆活活潑潑的心,他想打破砂鍋問到底,找尋生命的根源。他誠懇地向岩頭請法。
岩頭說:「你身上要是黏上了粢粑,你知道怎樣把它弄掉吧?」
黃龍爽快地回答:「知道。」
「那你就先把粢粑去掉吧!」
黃龍心頭一場霧:我向大師求法,卻這麼搪塞。心有點涼了,就向岩頭告辭。
走到玄泉那邊,他也問起佛法的根本。
玄泉隨手撿起一個皂角給他看,問他:「懂嗎?」
「不懂。」
玄泉拿著皂角,做出洗衣服的動作。
黃龍一看就向玄泉禮拜,並說:「啊!我明白了,佛法原來沒有差異。」
玄泉就問他:「你懂了什麼道理?」
海機回答:「我以前問過岩頭師父,他問我知道不知道怎樣把粢粑弄掉,弄掉粢粑就是去黏。師父您拿皂角也是要我去黏,所以我已明白佛法就是去黏,是沒有差別的。」
這些道理用常識判斷就知道是正確的,所以海機很有自信。佛法就是去黏,哪能說不對?
玄泉卻敞聲大笑。
笑聲裡,海機腦海一頓,空朗澄明,突然大悟了。佛法沒有大道理,岩頭也好,玄泉也好,他們要以「無言顯有言」,在電光石火中沖破了求法者內心層層的障礙,突破重重無明。
同樣的情節也發生在漸源仲興身上。
仲興是道吾的侍者。
一天,他們到檀越家弔慰。
仲興指著棺材問道吾:「是生?是死?」
道吾說:「生不也說,死也不說。」
「為什麼不說?」
道吾堅定地說:「不說,不說。」
回寺的途中,仲興沒好氣地對道吾說:「無論如何師父必須跟我說,要再不說,我就打你。」
「打就任你打吧!說是不說的。」道吾似乎發了牛脾氣,不肯告訴他。仲興掄起拳來打道吾。
以下犯上,仲興離開了道吾,找到一個小村的院子,隱居參悟。
三年後的一天,他聽到一個孩子在念〈普門品〉,有一句「應以比丘……身得度者,即現比丘……身」時,忽然大悟。
他焚香遙拜道吾:「我現在明白了師父的遺言不會是無緣無故,當時我沒有覺悟,卻錯怪了師父。其實師父當時已懇切地開示了。」
道吾以有言顯無言,直破仲興內心累積的疑團,而仲興不能領會,因此身負疑團三年不釋,直到聆聽〈普門品〉的剎那。平時誦經,滑溜而過,現在聽到他人誦經,卻那麼親切,
在腦中迴繞不息,毫無他念,頃刻擊破無明的枷鎖,頓入三昧,才深知佛法是離言語、離文字的。
你在唱而不唱的剎那,心情平靜祥和,不思善、不思惡,那個能覺知的是葉公畫龍而真龍出現。
「山前一片閒田地,叉手叮嚀問祖翁;
幾度賣來還自買,為憐松竹引清風。」
雖說「佛法無多子」是臨濟初悟的豪放,但以後多年的鉗錘,才能轉身而出,前途十八灘,灘灘險惡,是冰稜上行走啊!
那隻鷺鷥振翼飛起,像一朵白雲飄向遠遠的天際,倏忽不見,朗朗的是乾坤,朗朗是詠唱的心境。